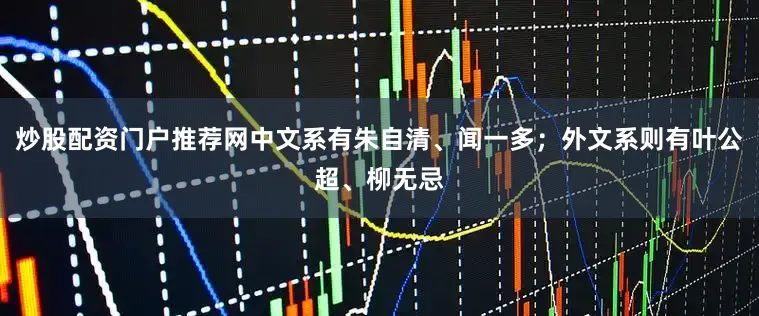
谈到民国,你能想到什么呢?
是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?
是军阀混战,强敌环伺?
还是林徽因的诗?
徐悲鸿的画?
穿旗袍的画报女郎?
亦或是五四青年的一声声呐喊?
革命先烈的慷慨激昂?
民国,就像狄更斯在《双城记》中开头说的:
“这是最好的时代,也是最坏的时代……是希望的春天,也是绝望的冬天……”
那个时代炮火连天,民不聊生,但也人才辈出,百家争鸣。
而西南联大,则是那个时代重要的人才摇篮。
那时的西南联大,飞机在头上轰炸,学生在洞里上课,但就是这样艰苦的环境,孕育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、8位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、171位两院院士以及100多位人文大师。
学生出俊杰,教授更是不遑多让。
担任常委的有清华校长梅贻琦、北大校长蒋梦麟、南开校长张伯苓,中文系有朱自清、闻一多;
外文系则有叶公超、柳无忌,哲学心理系有冯友兰、金岳霖,算学系有华罗庚,社会学系有费孝通……
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,则是当时西南联大的历史系教授、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。
郑天挺是西南联大的“大管家”,他在抗战期间担任西南联大的总务长,为学校的运营保驾护航。
他也是史学界的“当家”人物,为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建设恪尽职守。
他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,被誉为20世纪后期少有的宗师级史学家。
接下来,我们就一起走进郑天挺的传奇人生。

郑天挺,1899年8月9日出生,祖籍福建长乐。
长乐设县始于唐武德六年(623年),取长安久乐之义。
长乐历史文化底蕴深厚,自古就有“海滨邹鲁、文献名邦”的美誉。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良好的文化氛围,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。
古有“朱子理学第一传人”黄榦,明代数学家、珠算学家柯尚迁,清代著名中医理论家、医学教育家陈修园;
近现代则有作家郑振铎、诗人冰心等人物。
而郑天挺也是长乐这片土地培育出的一颗璀璨明星。
郑天挺出生于书香世家,他的曾祖父郑廷珪,是清代道光年间进士,之后先后到安吉、象山、金华等地当知县。
郑天挺父亲郑叔忱,继承了曾祖父的才学,在光绪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,也考中了进士,之后到翰林院任庶吉士。
庶吉士是明清两朝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,为皇帝近臣,是明朝内阁辅臣的重要来源之一,一般在进士当中选择最有潜质的人担任。
后来,郑叔忱于光绪二十八年后任奉天府丞、奉天学政、京师大学堂教务提调等职务。
郑天挺母亲陆嘉坤,也是一位知识女性,她“善作诗,操古琴”,有遗著《初日芙蓉楼吟稿》。
家学渊源为郑天挺今后的路铺就了基础,但其父母先后早逝。
父母托孤于亲戚梁济,之后郑天挺和弟弟就被寄养在姨父家,由梁济监护。
虽然双亲离世,又寄人篱下,但是郑天挺没有自怨自艾,他在学习上一直非常优秀,即使后来带着弟弟单独生活,也从来没有耽误学业。
他18岁的时候,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考入了北京大学国文系。
在北大,除了学习国文课程外,郑天挺还旁及其他专业的知识,在图书馆系统阅读了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史籍,培养出了对史学的浓厚兴趣。
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,郑天挺也参加了北大学生会组织的活动,还代表北大到天津与南开中学联络,也曾参与街头宣传活动。
他还与朱谦之、许地山等十四名在北京的福建籍学生成立了社会改革学会。
此时的郑天挺既是一个求知若渴的有志学子,也是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热血青年。
他尽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,探索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。
1920年夏天,21岁的郑天挺从北京大学毕业后,先后在北洋政府经济调查局、厦门大学有过短暂的任职经历。
一年后,郑天挺再次返回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,师从钱玄同。
在读研期间,郑天挺参与了北京大学主持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工作,这项工作也为他日后研究明清史奠定了基础。
研究生毕业后,郑天挺留校担任北京大学讲师,负责教授人文地理等课程。
在教学之余,他对于史学的兴趣愈加浓厚,并产生了“史宜立图”、纂集《史籍考》的愿望。
郑天挺担任北京大学讲师两年后。
他开始兼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员,以及外国语专门学校的教员。
但是好景不长,1926年3月,北洋政府卫队制造了318惨案。
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数名学生在惨案中死亡,加上北洋政府欠薪严重,一年后,郑天挺离开北大,转去浙江省民政厅和浙江大学任职。
直到1930年底,郑天挺才重回北大。
这次他出任北大秘书长,还兼任了中国文学系的教授,讲授古地理学和校勘学等课程,并且主持编辑了《古地理学讲义》,校勘《世说新语》。
三年后,他开始专注于明清史的研究。
1937年7月7日,七七事变爆发,北大师生纷纷离校南下。
在这种危急关头,郑天挺挑起料理校产和照顾未能脱身的教授们的重担,并组织学生安全撤退。
而他自己则临危不惧,照常办公,在日本宪兵队搜查北大办公室时,依然坚守岗位。
8月底,“汉奸维持会”派人接收北大,郑天挺才不得不离开校园,准备南下。
在南下的时候,他成了大家的领头羊。
他负责安排所有人的行程、管理图书、实验仪器的运输、经费筹措及使用等事项。
1937年11月,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。
但没过多久,由于长沙接连遭到敌机轰炸,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西迁昆明,并在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
到昆明后,由于校舍紧张,郑天挺代表北大赴蒙自,筹备在当地分设文学院、法学院的相关事宜。
在蒙自的半年期间,郑天挺除了教授隋唐五代史外,研究范围还涉及了西南边疆史和西藏史,先后写作了《发羌之地望与对音》等文章。
1938年下半年起,郑天挺开始在西南联大教授明清史。
1939年5月,北京大学恢复文科研究所,明清史研究室由郑天挺主持。
1940年初,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离职,清华校长梅贻琦等人均推荐郑天挺继任。
就职后,郑天挺开始忙于行政工作,负责处理联大各种复杂繁重的校务。
为了给西南联大筹措经费,他还经常奔波于兴文、富滇、劝业、矿业等银行。
可以说,西南联大能够在战火纷飞的时局下坚持办学,郑天挺厥功至伟。
郑天挺也因此被称为西南联大的“大管家”。
抗战结束后,1945年8月底,北大开始计划复校事宜,决定组织迁移委员会,郑天挺又受命返回北平接收校产。
可以说,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他始终为学校事务鞠躬尽瘁,尽职尽责。
郑天挺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弱书生,每逢危难之时,他总是挺身而出,义不容辞地担起重任,为其他师生保驾护航。
他身上体现了老一辈学者的使命感、责任感。
1952年9月,在北大教学7年后,郑天挺被调去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、中国史教研组主任,开始了其后半生长达三十年的南开生活。
当时南开大学在教学方面有诸多不完善之处,郑天挺到南开后,马不停蹄展开了改革,并亲自指定新的教学计划,亲自授课为其他教师做示范。
他还在南开大学创建了明清史研究室,主持了校点《明史》等重要学术工作,并培养了大批史学学子,壮大了历史学科的学术队伍。
不仅如此,怀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郑天挺还积极参与全国性的史学建设活动。
比如担任历史学科评议组的召集人,带领全国史学界编纂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,推动明清史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等,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。
虽然行政工作繁忙,但郑天挺从未脱离史学的教学和研究。
即使是在抗战期间,战火纷飞,他又忙于西南联大校务工作时,郑天挺也一直有史学报告、研究出世。
郑天挺在明清史、隋唐史、魏晋南北朝史、音韵学、历史地理等方面均有学术论著发表;
且著作形式多样,目前已出版的有学术专著1部,序跋文1篇,日记辑录1部。
学术论文集3部,演讲记录5部,学术论文11篇。
他的主要论著,包括《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》《清史探微》《探微集》《清史简述》等,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。
1981年,由于积劳成疾,郑天挺因病逝世于天津。
郑天挺的一生,是与时代同行、与学术共进的一生。
他既是民国时期学术精神的缩影,也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见证。
他以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严谨的治学态度,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,更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坚定的学术追求,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的一面旗帜。
他对于历史学的深刻研究和独到见解,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和精神财富。
九五配资-正规线上配资-武汉股票配资公司-炒股杠杆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